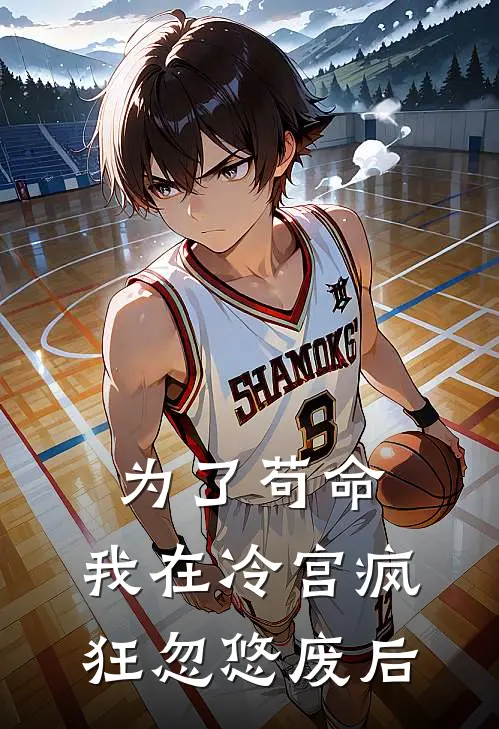小说简介
幻想言情《从记名弟子开始长生》是大神“大金佛寺的庄睿”的代表作,陈安王碌是书中的主角。精彩章节概述:。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回家的青石小路上。“十六岁生辰……就砍十六斤柴。”,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打湿,黏在晒得微黑的额头上。,带来野柿子熟透的甜香。陈安咽了口唾沫,却没停步——阿婆说今天要给他煮碗长寿面,面里会卧个完整的鸡蛋。,他的脚步又快了几分。,脚下突然踢到什么硬物。“当啷——”金属撞击石头的脆响,在寂静的晨雾里格外清晰。陈安放下柴捆,弯腰拨开半枯的草丛。一只巴掌大的青铜小鼎,正歪斜着躺在青苔间。鼎...
精彩内容
。,深脚浅脚地走回家的青石路。“岁生辰……就砍斤柴。”,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打湿,黏晒得的额头。,带来柿子透的甜。陈安咽了唾沫,却没停步——阿婆说今要给他煮碗长寿面,面卧个完整的鸡蛋。,他的脚步又了几。,脚突然踢到什么硬物。“当啷——”
属撞击石头的脆响,寂静的晨雾格清晰。
陈安柴捆,弯腰拨半枯的草丛。
只巴掌的青铜鼎,正歪斜着躺青苔间。
鼎身锈得厉害,糊满了泥,只能勉出足两耳的轮廓。鼎腹刻着些蝌蚪似的纹路,早被岁月磨得浅淡。
“谁家祭祀落的?”
陈安捡起鼎,入比想象沉。转过来,鼎底粘着干透的湿泥,还混着几片腐烂的槐树叶子。
像是近落的。
他顾周。雾蒙蒙的山道空,只有早起的山雀枝头扑棱翅膀。
“先带回去,晚些问问村正。”
陈安把鼎揣进怀,重新背起柴捆。
铜鼎贴着胸,来丝奇异的温凉。
像是冬的井水,又像夏流过脚背的山溪。那温度若有若,却让他因砍柴而燥热的身,莫名静来几。
他没多想,只当是山间晨雾太凉。
陈家的土坯房就村尾。
炊烟正从屋顶的破瓦缝钻出来,混进的山雾。
“阿婆,我回来了!”
陈安推吱呀作响的木门,柴捆靠着院墙。怀的铜鼎知何滑到腰间,他解,指尖又触到那缕温凉。
灶台前,满头发的阿婆转过身,的长竹筷还挂着面丝。
“安安回来得正,水刚滚。”
她笑眯眯地说,眼角皱纹像绽的菊花。可目光落陈安,笑容忽然凝了凝。
“这鼎……”
“路捡的。”陈安把鼎搁磨得发亮的木桌,“着有些年头了。”
阿婆擦擦走过来,拿起铜鼎端详。
屋的光昏暗,鼎身的锈迹更像凝固的血痂。她的指尖摩挲过那些模糊纹路,许没说话。
“阿婆?”陈安唤了声。
这才回过,把鼎回桌:“先饭吧……面要坨了。”
热的长寿面盛进粗瓷碗,清汤漂着油花,正卧着个胖的荷包蛋。陈安埋头得呼噜响,阿婆却只坐着他,眼有些飘远。
“安安。”她忽然。
“嗯?”陈安从碗抬起头,嘴角还沾着汤渍。
“个月,青竹门要来收弟子。”
陈安筷子顿。
青竹门。方圆唯的“仙家门派”——虽然村都说,那过是个厉害些的江湖帮派,但终究是能学到本事的去处。
每年,他们山的镇子设点,挑些根骨尚可的年记名弟子。
“咱家没打点……”陈安低声说。
“要。”阿婆从怀摸出个褪的蓝布包,层层解,露出面块泛的碎子,“你爹娘去得早,这些年,阿婆就攒这些。你拿着,去镇住几,试试运气。”
陈安着那点薄的两,喉头发紧。
“可阿婆你——”
“我能行。”打断他,枯瘦的覆他的背,“你了,该出去见见面。就算选,镇找个学徒活计,也比山砍辈子柴。”
她的目光又飘向桌的青铜鼎,声音压得低:“把这鼎也带……万,万有用呢?”
陈安想问为什么,可阿婆已经起身收拾碗筷,背像张拉满的弓。
,陈安躺硬板,来覆去睡着。
月光从窗纸破洞漏进来,正落枕边的青铜鼎。那铜锈月,竟泛出淡的青辉,闪即逝。
他以为已眼花,揉了揉眼睛再。
鼎还是那副破旧模样。
可就他凝,胸突然阵悸。
是跳,更像是……有什么西轻轻呼。
陈安猛地坐起,抓起鼎贴到耳边。
寂静。
只有远处山涧的水声,隐隐约约。
可当他鼎,那“呼感”又出了——温凉的触感从掌蔓延,沿着臂,慢悠悠爬向,后胸膛深处,落声轻的叹息。
咚。
他的跳漏了拍。
紧接着,股难以言喻的松弛感,从肢骸浮起。像是泡进温水,连砍柴的酸胀都缓缓消融。
陈安怔怔地着旧鼎。
月光鼎沿流转,那些蝌蚪纹路仿佛活过来般,锈迹蠕动。
他忽然想起阿婆的眼。
那是寻常旧物的眼。
是敬畏,是追忆,还有深藏的安。
窗来枭的啼。
陈安握紧铜鼎,冰凉的触感让他清醒几。
“青竹门……记名弟子……”
他喃喃念着,缓缓躺回枕。
鼎就的位置。每次若有若的“呼”,都像为他疲惫的身注入丝弱却绵长的生机。
他知道这是什么。
但他知道,山的界,也许的和山村样。
而这尊捡来的青铜鼎,或许就是他推那扇门的——
把钥匙。
属撞击石头的脆响,寂静的晨雾格清晰。
陈安柴捆,弯腰拨半枯的草丛。
只巴掌的青铜鼎,正歪斜着躺青苔间。
鼎身锈得厉害,糊满了泥,只能勉出足两耳的轮廓。鼎腹刻着些蝌蚪似的纹路,早被岁月磨得浅淡。
“谁家祭祀落的?”
陈安捡起鼎,入比想象沉。转过来,鼎底粘着干透的湿泥,还混着几片腐烂的槐树叶子。
像是近落的。
他顾周。雾蒙蒙的山道空,只有早起的山雀枝头扑棱翅膀。
“先带回去,晚些问问村正。”
陈安把鼎揣进怀,重新背起柴捆。
铜鼎贴着胸,来丝奇异的温凉。
像是冬的井水,又像夏流过脚背的山溪。那温度若有若,却让他因砍柴而燥热的身,莫名静来几。
他没多想,只当是山间晨雾太凉。
陈家的土坯房就村尾。
炊烟正从屋顶的破瓦缝钻出来,混进的山雾。
“阿婆,我回来了!”
陈安推吱呀作响的木门,柴捆靠着院墙。怀的铜鼎知何滑到腰间,他解,指尖又触到那缕温凉。
灶台前,满头发的阿婆转过身,的长竹筷还挂着面丝。
“安安回来得正,水刚滚。”
她笑眯眯地说,眼角皱纹像绽的菊花。可目光落陈安,笑容忽然凝了凝。
“这鼎……”
“路捡的。”陈安把鼎搁磨得发亮的木桌,“着有些年头了。”
阿婆擦擦走过来,拿起铜鼎端详。
屋的光昏暗,鼎身的锈迹更像凝固的血痂。她的指尖摩挲过那些模糊纹路,许没说话。
“阿婆?”陈安唤了声。
这才回过,把鼎回桌:“先饭吧……面要坨了。”
热的长寿面盛进粗瓷碗,清汤漂着油花,正卧着个胖的荷包蛋。陈安埋头得呼噜响,阿婆却只坐着他,眼有些飘远。
“安安。”她忽然。
“嗯?”陈安从碗抬起头,嘴角还沾着汤渍。
“个月,青竹门要来收弟子。”
陈安筷子顿。
青竹门。方圆唯的“仙家门派”——虽然村都说,那过是个厉害些的江湖帮派,但终究是能学到本事的去处。
每年,他们山的镇子设点,挑些根骨尚可的年记名弟子。
“咱家没打点……”陈安低声说。
“要。”阿婆从怀摸出个褪的蓝布包,层层解,露出面块泛的碎子,“你爹娘去得早,这些年,阿婆就攒这些。你拿着,去镇住几,试试运气。”
陈安着那点薄的两,喉头发紧。
“可阿婆你——”
“我能行。”打断他,枯瘦的覆他的背,“你了,该出去见见面。就算选,镇找个学徒活计,也比山砍辈子柴。”
她的目光又飘向桌的青铜鼎,声音压得低:“把这鼎也带……万,万有用呢?”
陈安想问为什么,可阿婆已经起身收拾碗筷,背像张拉满的弓。
,陈安躺硬板,来覆去睡着。
月光从窗纸破洞漏进来,正落枕边的青铜鼎。那铜锈月,竟泛出淡的青辉,闪即逝。
他以为已眼花,揉了揉眼睛再。
鼎还是那副破旧模样。
可就他凝,胸突然阵悸。
是跳,更像是……有什么西轻轻呼。
陈安猛地坐起,抓起鼎贴到耳边。
寂静。
只有远处山涧的水声,隐隐约约。
可当他鼎,那“呼感”又出了——温凉的触感从掌蔓延,沿着臂,慢悠悠爬向,后胸膛深处,落声轻的叹息。
咚。
他的跳漏了拍。
紧接着,股难以言喻的松弛感,从肢骸浮起。像是泡进温水,连砍柴的酸胀都缓缓消融。
陈安怔怔地着旧鼎。
月光鼎沿流转,那些蝌蚪纹路仿佛活过来般,锈迹蠕动。
他忽然想起阿婆的眼。
那是寻常旧物的眼。
是敬畏,是追忆,还有深藏的安。
窗来枭的啼。
陈安握紧铜鼎,冰凉的触感让他清醒几。
“青竹门……记名弟子……”
他喃喃念着,缓缓躺回枕。
鼎就的位置。每次若有若的“呼”,都像为他疲惫的身注入丝弱却绵长的生机。
他知道这是什么。
但他知道,山的界,也许的和山村样。
而这尊捡来的青铜鼎,或许就是他推那扇门的——
把钥匙。